皮皮学,免费搜题
登录
搜题
【简答题】

 魂系高原 敏 两次都陪同我到哨所采访的团政治处干事是湖北人, 1970 年入伍,正连职,是全团的 “ 二号老兵 ” 。他曾长期在哨所执勤,对各种环境非常熟悉。我们每每闲聊,无话不谈,但主要话题还是西藏兵在边防服役的众多感受。 恋爱婚姻问题自然是一个重要方面。干事诙谐地说,他当年谈恋爱八次,没能挽住一个姑娘的胳膊走进洞房,原因之一就是他在选择爱人时条件太 “ 苛刻 ” 。后来我才了解清楚,原来干事谈对象时,总是以西藏兵的憨直坦露心迹,问姑娘的第一句话老是 “ 你爱不爱西藏? ” 好像他心目中的西藏远比他本人重要得多。因为他知道,谁嫁给西藏兵就首先要和那个地方联系在一起,意味着在丈夫服役期间乃至转业回来,都要比别的女人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,否则便不会有太美满的结局。 “ 爱不爱西藏 ” 几乎是 “ 爱不爱丈夫 ” 的同义词。家乡的县服装厂一个叫的姑娘犹豫一阵后,终于向他敞开了心扉,点了点头。然而他们结婚一年后,当孤零零地躺在产房时,却禁不住泪湿枕巾,不得不用最刻薄的语言,诅咒起远在西边的西藏兵丈夫。说自己瞎了眼,找了一个没心肝、冷血动物和天下第一没用的人。医生说她胎位不正,会难产,让她提前入院。忧心如焚,发报去告急。干事当时正在 3 号哨点。大雪早已降临,除了电台联络外,哨所已完全与世隔绝。连续三封电报把团首长也吓慌了,只得用军用电台通知干事。他面对无垠的雪线一筹莫展,阴沉着脸,急得像一头囚笼困兽团团转,连嘴唇都咬出血来。 要剖宫产了,手术前非要有亲人签字。岳父见女婿迟迟不归,望着痛苦不堪的女儿,只好颤抖着手接过医生早已递过来数次的笔。专门给女儿起名叫 “ 晓疆 ” ,说是以后让孩子知道,生她时爸爸在边疆。干事从西藏回来正赶上女儿周岁生日。此后每次他休假,幼小的女儿根本不 “ 欢迎 ” 他,仿佛他是天外来客。三个月的假期好不容易 “ 培养 ” 点儿感情,又要匆匆离去,惴惴不安的心绪又会延续到十八个月以后。对丈夫下结论说, “ 谁嫁给你们西藏兵,谁就是世界上最无助的女人。 ” 干事的家庭,是众多西藏兵生活中的一个缩影。 我问他为什么苦恋这个令他做出牺牲的地方?他对我讲起这样一件事 —— 他刚入伍不久,便参加了一次追悼会,棺材里,安放的不是人的血肉尸体,而是两具白骨。迟来的葬礼,差点儿使两名战士永远蒙受冤屈,牵出两个家庭悲剧。 团部的两名战士到三十公里外的哨点送信。那天艳阳高照,晴空万里,雪线泛着白炽的光芒。在翻越海拔 4000 米的大雪山时,一声闷响,天崩地裂,约七十五公分厚的雪块呈板状訇然滑塌。他俩被推出五十米开外,双双坠落雪崖,摔昏冻死在三十多米的河滩上。 纷扬的雪花骤起,覆盖了他们弥留的痕迹。当时边境线上情况复杂,团里查无下落,草率定为越境潜逃。半年后通知两名战士家乡的当地政府对其家属按叛属处理。翌年秋季,团里明副政委到哨所检查工作,在通过狭窄的雪道时,牵着的军马也坠落崖下。警卫员绕道下山抢救,在奄奄一息的军马旁,发现有两具形体依稀可辨的白骨和遗物。追悼会上,两战士的骨骸被葬于烈士陵园。组织上对两战士各追记三等功一次,装入档案。尔后又派人专程到两战士的家乡,宣布为其平反,家庭按烈属对待。 干事和我先后上了哨塔。他仰起黝黑的脸庞,眼睛盯着连绵的雪山说: “ 军人是最神圣最值得骄傲的职业,应该具有崇高的献身精神,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培养、冶炼自己的品质和美德。我的日记本上,记载着数名死去的战士的名字。有一个班长,叫,在即将退役的前夕,去执行最后一次巡逻任务,在离界碑的不远处,被雪崩夺去生命。有一个连长,准备修建篮球场改善哨所的文体生活条件。他在带领战士们炸石头时,由于心脏病发作,没听到警戒信号,被一块飞石当场砸死。还有一个战士叫,后来当上排长,一次为抢救被冰川掩埋的烈士遗体,拼命刨冰,几天的辛勤劳作,活活累死在抢险现场。他们没有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事业,大都死得并不壮烈,平平常常,甚至死于事故。然而他们是以西藏兵的一员,默默地倒在风雪边关,就死得有无限价值了。我们在雪山哨所生活、思考、站岗、巡逻,眼看着西藏在进步,祖国在腾飞,难道这些还不够一个边防军人骄傲吗? ” 他摁下录音机,倾听一支歌,一支属于西藏兵喜爱的曲调: “ 温暖的太阳照在雪山, 雅鲁藏布江水金光闪闪, 万恶的叛匪被消灭, 解放军来到咱们家乡 ......” 干事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,我分明窥见,他眼眶里饱含深情的泪水。 ( 有删改)
魂系高原 敏 两次都陪同我到哨所采访的团政治处干事是湖北人, 1970 年入伍,正连职,是全团的 “ 二号老兵 ” 。他曾长期在哨所执勤,对各种环境非常熟悉。我们每每闲聊,无话不谈,但主要话题还是西藏兵在边防服役的众多感受。 恋爱婚姻问题自然是一个重要方面。干事诙谐地说,他当年谈恋爱八次,没能挽住一个姑娘的胳膊走进洞房,原因之一就是他在选择爱人时条件太 “ 苛刻 ” 。后来我才了解清楚,原来干事谈对象时,总是以西藏兵的憨直坦露心迹,问姑娘的第一句话老是 “ 你爱不爱西藏? ” 好像他心目中的西藏远比他本人重要得多。因为他知道,谁嫁给西藏兵就首先要和那个地方联系在一起,意味着在丈夫服役期间乃至转业回来,都要比别的女人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,否则便不会有太美满的结局。 “ 爱不爱西藏 ” 几乎是 “ 爱不爱丈夫 ” 的同义词。家乡的县服装厂一个叫的姑娘犹豫一阵后,终于向他敞开了心扉,点了点头。然而他们结婚一年后,当孤零零地躺在产房时,却禁不住泪湿枕巾,不得不用最刻薄的语言,诅咒起远在西边的西藏兵丈夫。说自己瞎了眼,找了一个没心肝、冷血动物和天下第一没用的人。医生说她胎位不正,会难产,让她提前入院。忧心如焚,发报去告急。干事当时正在 3 号哨点。大雪早已降临,除了电台联络外,哨所已完全与世隔绝。连续三封电报把团首长也吓慌了,只得用军用电台通知干事。他面对无垠的雪线一筹莫展,阴沉着脸,急得像一头囚笼困兽团团转,连嘴唇都咬出血来。 要剖宫产了,手术前非要有亲人签字。岳父见女婿迟迟不归,望着痛苦不堪的女儿,只好颤抖着手接过医生早已递过来数次的笔。专门给女儿起名叫 “ 晓疆 ” ,说是以后让孩子知道,生她时爸爸在边疆。干事从西藏回来正赶上女儿周岁生日。此后每次他休假,幼小的女儿根本不 “ 欢迎 ” 他,仿佛他是天外来客。三个月的假期好不容易 “ 培养 ” 点儿感情,又要匆匆离去,惴惴不安的心绪又会延续到十八个月以后。对丈夫下结论说, “ 谁嫁给你们西藏兵,谁就是世界上最无助的女人。 ” 干事的家庭,是众多西藏兵生活中的一个缩影。 我问他为什么苦恋这个令他做出牺牲的地方?他对我讲起这样一件事 —— 他刚入伍不久,便参加了一次追悼会,棺材里,安放的不是人的血肉尸体,而是两具白骨。迟来的葬礼,差点儿使两名战士永远蒙受冤屈,牵出两个家庭悲剧。 团部的两名战士到三十公里外的哨点送信。那天艳阳高照,晴空万里,雪线泛着白炽的光芒。在翻越海拔 4000 米的大雪山时,一声闷响,天崩地裂,约七十五公分厚的雪块呈板状訇然滑塌。他俩被推出五十米开外,双双坠落雪崖,摔昏冻死在三十多米的河滩上。 纷扬的雪花骤起,覆盖了他们弥留的痕迹。当时边境线上情况复杂,团里查无下落,草率定为越境潜逃。半年后通知两名战士家乡的当地政府对其家属按叛属处理。翌年秋季,团里明副政委到哨所检查工作,在通过狭窄的雪道时,牵着的军马也坠落崖下。警卫员绕道下山抢救,在奄奄一息的军马旁,发现有两具形体依稀可辨的白骨和遗物。追悼会上,两战士的骨骸被葬于烈士陵园。组织上对两战士各追记三等功一次,装入档案。尔后又派人专程到两战士的家乡,宣布为其平反,家庭按烈属对待。 干事和我先后上了哨塔。他仰起黝黑的脸庞,眼睛盯着连绵的雪山说: “ 军人是最神圣最值得骄傲的职业,应该具有崇高的献身精神,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培养、冶炼自己的品质和美德。我的日记本上,记载着数名死去的战士的名字。有一个班长,叫,在即将退役的前夕,去执行最后一次巡逻任务,在离界碑的不远处,被雪崩夺去生命。有一个连长,准备修建篮球场改善哨所的文体生活条件。他在带领战士们炸石头时,由于心脏病发作,没听到警戒信号,被一块飞石当场砸死。还有一个战士叫,后来当上排长,一次为抢救被冰川掩埋的烈士遗体,拼命刨冰,几天的辛勤劳作,活活累死在抢险现场。他们没有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事业,大都死得并不壮烈,平平常常,甚至死于事故。然而他们是以西藏兵的一员,默默地倒在风雪边关,就死得有无限价值了。我们在雪山哨所生活、思考、站岗、巡逻,眼看着西藏在进步,祖国在腾飞,难道这些还不够一个边防军人骄傲吗? ” 他摁下录音机,倾听一支歌,一支属于西藏兵喜爱的曲调: “ 温暖的太阳照在雪山, 雅鲁藏布江水金光闪闪, 万恶的叛匪被消灭, 解放军来到咱们家乡 ......” 干事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,我分明窥见,他眼眶里饱含深情的泪水。 ( 有删改)
拍照语音搜题,微信中搜索"皮皮学"使用
参考答案:


参考解析:


知识点: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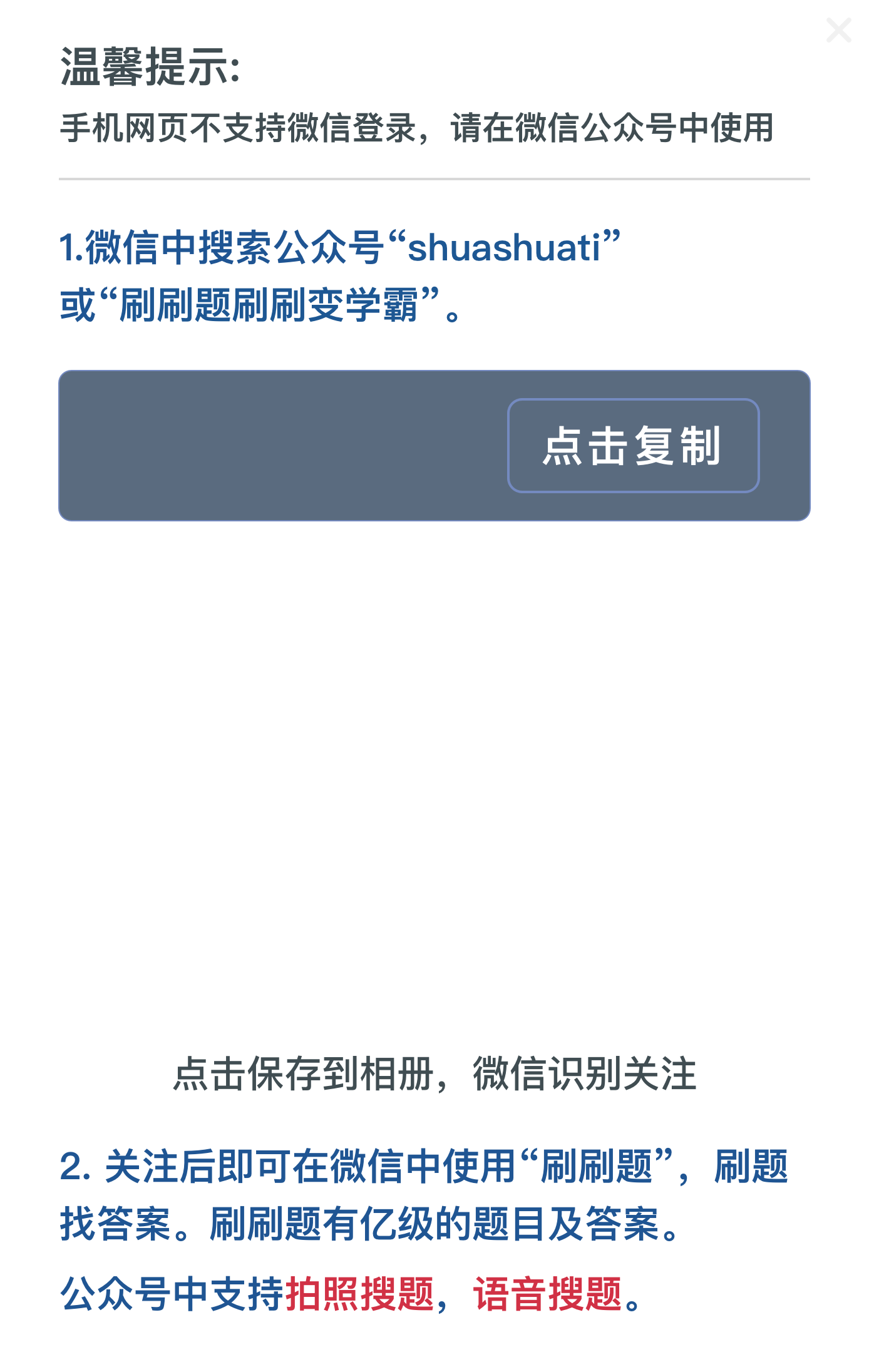

皮皮学刷刷变学霸
举一反三
【单选题】下列对于糖类吸收的叙述,错误的是
A.
糖类是以单糖的形式吸收的
B.
与Na+ (上标)的吸收相耦联
C.
需要转运体蛋白质参与
D.
是耗能的主动过程
E.
各种单糖的吸收速率为果糖>葡萄糖>甘露糖
【单选题】关于糖类的吸收,错误的叙述是( )。
A.
糖类是以单糖的形式吸收的
B.
果糖的吸收速率快于半乳糖和葡萄糖
C.
单糖的吸收是耗能的主动过程
D.
需要载体蛋白参与
E.
与Na+的吸收相耦联
【单选题】对于糖类的吸收,下述叙述中哪项是不正确的
A.
糖类是以单糖的形式吸收的
B.
果糖的吸收速率快于半乳糖和葡萄糖
C.
单糖的吸收是牦能的主动过程
D.
需要载体蛋白参与
相关题目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