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皮学,免费搜题
登录
搜题
【简答题】

 回到诊所后,我决定坐候老板回来。同时,也竭力使自己觉得,自己并不事业尚未起步之前就把一切搞砸了。回想一切细节,我知道我别无选择,不论我回想多少次,结论总是一样的。 清晨1点西格才回来,它与他老母共度的黄昏一定是愉快的。他瘦脸发光,微带酒气。我没想到他还穿了正式的晚装,虽说上身式样老旧,挂在它的瘦骨架上显得晃荡,不过整个人看起来倒像个大使哩。 西格静静地听完了我报告他的有关病马的种种情况。他正在说什么的时候,电话铃响了。“哦,是你。”他朝我点点头,坐下,然后又好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说:“是的。”“不是的。”“哦。”最后他带有决定性地坐直了,说道:“,谢谢你打电话来,看来哈利先生做了再当时情形之下唯一能做的事。不,我不能同意,让病马自生自灭是太残忍了。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减轻痛苦。很遗憾你那么想,我个人认为哈利先生是一位能力非常强的兽医。当时若是我在场的话,毫无疑问我也会那么做。晚安,,明早见。” 我一下子好过了许多,几乎想开口演说一段致谢辞,而我真正说出口的,只是“谢谢”二字。 西格站起来从火炉上的架子拿下来一瓶威士忌,他给我倒了小半杯,也给自己倒了些,于是重新坐下。 他喝了一口,盯住杯中的琥珀液体约数秒钟,然后他笑了:“好呀,你今晚可真碰上了!你的第一个病例,还偏偏是姓的。” “你同他很熟吗?” “嗯,他的那些我。相信我,他可不是我的什么朋友。事实上,有人传谣他是个贼。有人说他中饱私囊,揩主人的油已经很久了。我想总有一天他会失手的。” 威士忌像一团火似的直烧到我的胃里,不过我觉得很受用。“我可不希望常常有这种事发生,不过我想兽医这一行也不至于天天如此。” “不至于。”西格说,“不过你也永远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你。我们这行相当滑稽,给你无可比拟的机会让给你做傻瓜。” “我以为得看各人的能力而定。” “到某一程度而言,的确是如此。能力强可以帮你把工作做得好。不过,即使你是个正牌天才,羞辱耻笑也不定什么时候回落到你的身上。我又一次请了一位鼎鼎有名的医马专家到此地来开一个刀,那匹马在开了一半的当口死掉了。眼看着专家狂怒地跳个不停,可让我明白了一条真理:就是说,我自己也会不时地当当傻瓜。” 我笑了:“那我最好现在就退出这行算了。” “就是这么说,动物都是难以预料的,所以我们这一生也是难以预知的,是一连串的小成功跟小失败加起来的。你得真心爱这一行才撑得下去。今天是姓的,明天又可能是别人。只有一样靠得住,就是你永不会觉得单调无聊。来,再喝一点。” 我们又喝又谈,不知不觉窗外的树影已经在灰白色的天空里显现出来了,一只小鸟正在试吹新调。西格打了一个哈欠,把黑领结解下来,看看表,说:“哎,都 5 点了,谁想得到?我很高兴我们在一起喝了一杯,正好庆祝你的开张第一炮,你说是不是?” —— 摘自《万物既伟大又渺小》
回到诊所后,我决定坐候老板回来。同时,也竭力使自己觉得,自己并不事业尚未起步之前就把一切搞砸了。回想一切细节,我知道我别无选择,不论我回想多少次,结论总是一样的。 清晨1点西格才回来,它与他老母共度的黄昏一定是愉快的。他瘦脸发光,微带酒气。我没想到他还穿了正式的晚装,虽说上身式样老旧,挂在它的瘦骨架上显得晃荡,不过整个人看起来倒像个大使哩。 西格静静地听完了我报告他的有关病马的种种情况。他正在说什么的时候,电话铃响了。“哦,是你。”他朝我点点头,坐下,然后又好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说:“是的。”“不是的。”“哦。”最后他带有决定性地坐直了,说道:“,谢谢你打电话来,看来哈利先生做了再当时情形之下唯一能做的事。不,我不能同意,让病马自生自灭是太残忍了。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减轻痛苦。很遗憾你那么想,我个人认为哈利先生是一位能力非常强的兽医。当时若是我在场的话,毫无疑问我也会那么做。晚安,,明早见。” 我一下子好过了许多,几乎想开口演说一段致谢辞,而我真正说出口的,只是“谢谢”二字。 西格站起来从火炉上的架子拿下来一瓶威士忌,他给我倒了小半杯,也给自己倒了些,于是重新坐下。 他喝了一口,盯住杯中的琥珀液体约数秒钟,然后他笑了:“好呀,你今晚可真碰上了!你的第一个病例,还偏偏是姓的。” “你同他很熟吗?” “嗯,他的那些我。相信我,他可不是我的什么朋友。事实上,有人传谣他是个贼。有人说他中饱私囊,揩主人的油已经很久了。我想总有一天他会失手的。” 威士忌像一团火似的直烧到我的胃里,不过我觉得很受用。“我可不希望常常有这种事发生,不过我想兽医这一行也不至于天天如此。” “不至于。”西格说,“不过你也永远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你。我们这行相当滑稽,给你无可比拟的机会让给你做傻瓜。” “我以为得看各人的能力而定。” “到某一程度而言,的确是如此。能力强可以帮你把工作做得好。不过,即使你是个正牌天才,羞辱耻笑也不定什么时候回落到你的身上。我又一次请了一位鼎鼎有名的医马专家到此地来开一个刀,那匹马在开了一半的当口死掉了。眼看着专家狂怒地跳个不停,可让我明白了一条真理:就是说,我自己也会不时地当当傻瓜。” 我笑了:“那我最好现在就退出这行算了。” “就是这么说,动物都是难以预料的,所以我们这一生也是难以预知的,是一连串的小成功跟小失败加起来的。你得真心爱这一行才撑得下去。今天是姓的,明天又可能是别人。只有一样靠得住,就是你永不会觉得单调无聊。来,再喝一点。” 我们又喝又谈,不知不觉窗外的树影已经在灰白色的天空里显现出来了,一只小鸟正在试吹新调。西格打了一个哈欠,把黑领结解下来,看看表,说:“哎,都 5 点了,谁想得到?我很高兴我们在一起喝了一杯,正好庆祝你的开张第一炮,你说是不是?” —— 摘自《万物既伟大又渺小》
拍照语音搜题,微信中搜索"皮皮学"使用
参考答案:


参考解析:


知识点: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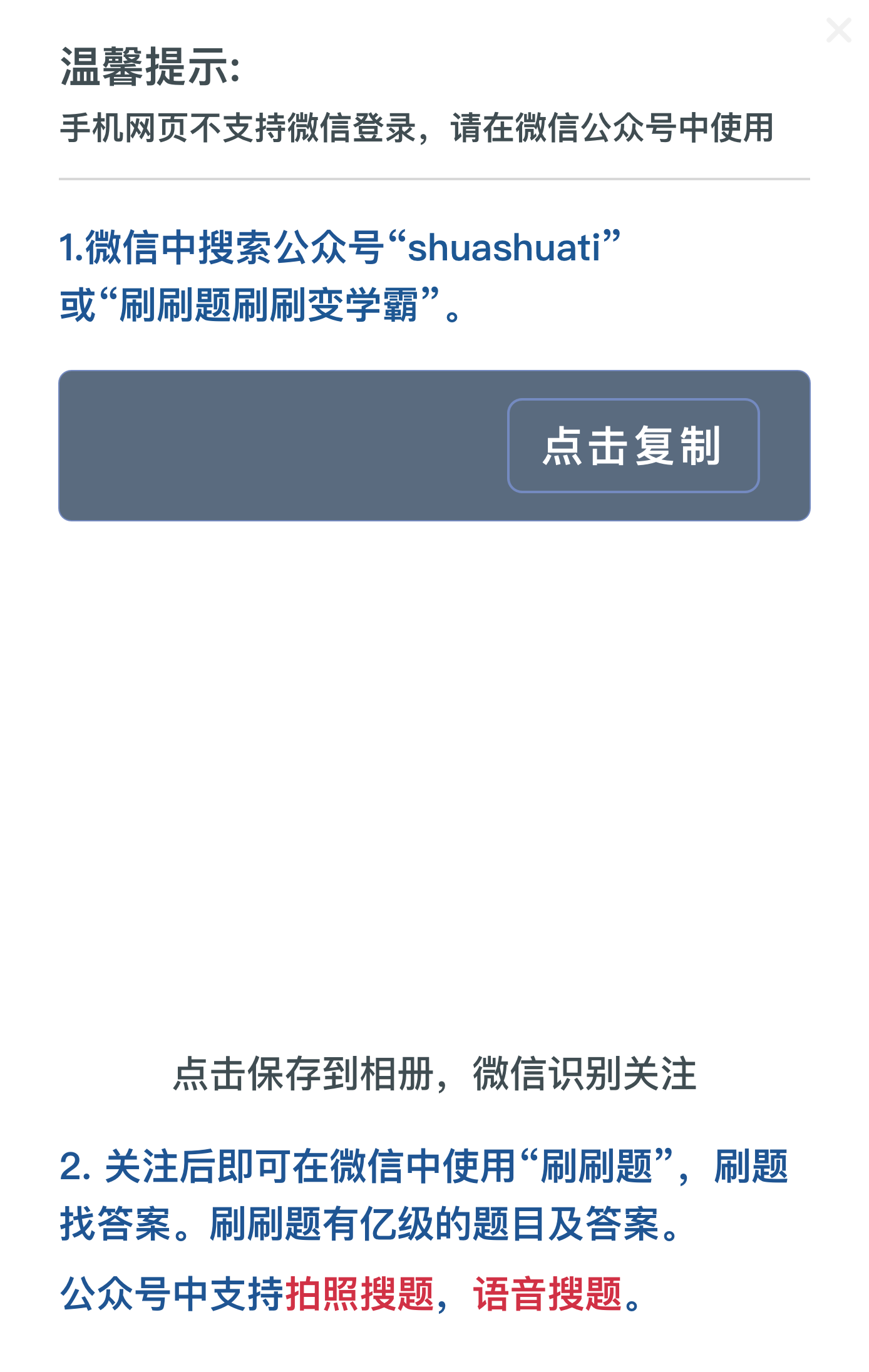

皮皮学刷刷变学霸
举一反三
【单选题】搜索草莓味或巧克力味的冰激凌,应该使用以下哪组检索词( )
A.
草莓 + 巧克力 + 冰激凌
B.
(草莓 | 巧克力) + 冰激凌
C.
冰激凌 | 巧克力 | 草莓
D.
(冰激凌 | 草莓) + (冰激凌 | 巧克力)
【单选题】关于酒店常见餐饮设施及服务项目的叙述,错误的是
A.
客房送餐部一般设在咖啡厅厨房附近,以方便备餐
B.
酒廊通常在中餐厅、西餐厅各种娱乐设施中设置
C.
咖啡厅的装饰主题以西式风格为主,并采用西式服务
D.
外卖酒吧是宴会酒吧中的一种特殊形式,是临时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