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皮学,免费搜题
登录
搜题
【简答题】

 先生记 先生家里的花瓶,好像画上所见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,灰蓝色,有点从瓷釉自然堆起的纹痕,瓶口的两边,还有两个小瓶耳,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青。 我第一次看到这花的时候,我就问过:“这叫什么名字?屋中既不生火炉,也不冻死?” 第一次,走进先生的家里去,那时快接近黄昏的时节,而且是个冬天,所以那楼下室稍微有一点暗,同时先生的纸烟,当它离开嘴边而停在桌角的地方,纹的卷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的发梢那么高。而且再升腾到就看不见了。 “这花,叫‘万年青’,永久这样!”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,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,的烟火,就越发红了,好像一朵小花似的,和他的袖口距离着。 “这花不怕冻?”以后,我又问过,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了。 说:“不怕的,最耐久!”而且她还拿着瓶口给我摇着。 我看到了花瓶的底边是一些圆石子。以后,因为熟识了的缘故,我就自己动手看过一两次,又加上这花瓶是常常摆在客厅的黑色长桌上;又加上自己是来自寒带的地方,对于这在四季里都不凋零的植物,总带有一点惊奇。 而现在这“万年青”依旧活着,每次到家去,看到,有时仍站在那黑色的长桌上,有时站在先生照像的前面。 花瓶是换了,用一个玻璃瓶装着,看得到淡黄色的须根,站在瓶底。 有时候一面和我们谈论着,一面检查着房中所有的花草。看一看叶子是不是黄了,该剪掉的剪掉,该洒水的洒水,因为不停地动作是她的习惯。有时候就检查着“万年青”,有时候就谈着先生,就在他的照像前面谈着,但那感觉,却像谈着古人那么悠远了。 至于瓶呢?站在墓地的青草上面去了,而且瓶底已经丢失,虽然丢失了也就让它空空地站在墓边。我所看到的是从春天一直站到秋天;它一直站到邻旁墓头的石榴树开了花而后结成了石榴。 从开炮以后,只有绕道去过一次,别人就没有去过。当然那墓草是长得很高了,而且荒了,还说什么花瓶,恐怕先生的瓷半身像也要被荒了的草埋没到他的胸口。 我们在这边,只能写纪念先生的文章,而谁去努力剪齐墓上的荒草?我们是越去越远了,但无论多么远,那荒草总是要记在心上的。
先生记 先生家里的花瓶,好像画上所见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,灰蓝色,有点从瓷釉自然堆起的纹痕,瓶口的两边,还有两个小瓶耳,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青。 我第一次看到这花的时候,我就问过:“这叫什么名字?屋中既不生火炉,也不冻死?” 第一次,走进先生的家里去,那时快接近黄昏的时节,而且是个冬天,所以那楼下室稍微有一点暗,同时先生的纸烟,当它离开嘴边而停在桌角的地方,纹的卷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的发梢那么高。而且再升腾到就看不见了。 “这花,叫‘万年青’,永久这样!”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,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,的烟火,就越发红了,好像一朵小花似的,和他的袖口距离着。 “这花不怕冻?”以后,我又问过,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了。 说:“不怕的,最耐久!”而且她还拿着瓶口给我摇着。 我看到了花瓶的底边是一些圆石子。以后,因为熟识了的缘故,我就自己动手看过一两次,又加上这花瓶是常常摆在客厅的黑色长桌上;又加上自己是来自寒带的地方,对于这在四季里都不凋零的植物,总带有一点惊奇。 而现在这“万年青”依旧活着,每次到家去,看到,有时仍站在那黑色的长桌上,有时站在先生照像的前面。 花瓶是换了,用一个玻璃瓶装着,看得到淡黄色的须根,站在瓶底。 有时候一面和我们谈论着,一面检查着房中所有的花草。看一看叶子是不是黄了,该剪掉的剪掉,该洒水的洒水,因为不停地动作是她的习惯。有时候就检查着“万年青”,有时候就谈着先生,就在他的照像前面谈着,但那感觉,却像谈着古人那么悠远了。 至于瓶呢?站在墓地的青草上面去了,而且瓶底已经丢失,虽然丢失了也就让它空空地站在墓边。我所看到的是从春天一直站到秋天;它一直站到邻旁墓头的石榴树开了花而后结成了石榴。 从开炮以后,只有绕道去过一次,别人就没有去过。当然那墓草是长得很高了,而且荒了,还说什么花瓶,恐怕先生的瓷半身像也要被荒了的草埋没到他的胸口。 我们在这边,只能写纪念先生的文章,而谁去努力剪齐墓上的荒草?我们是越去越远了,但无论多么远,那荒草总是要记在心上的。
拍照语音搜题,微信中搜索"皮皮学"使用
参考答案:


参考解析:


知识点: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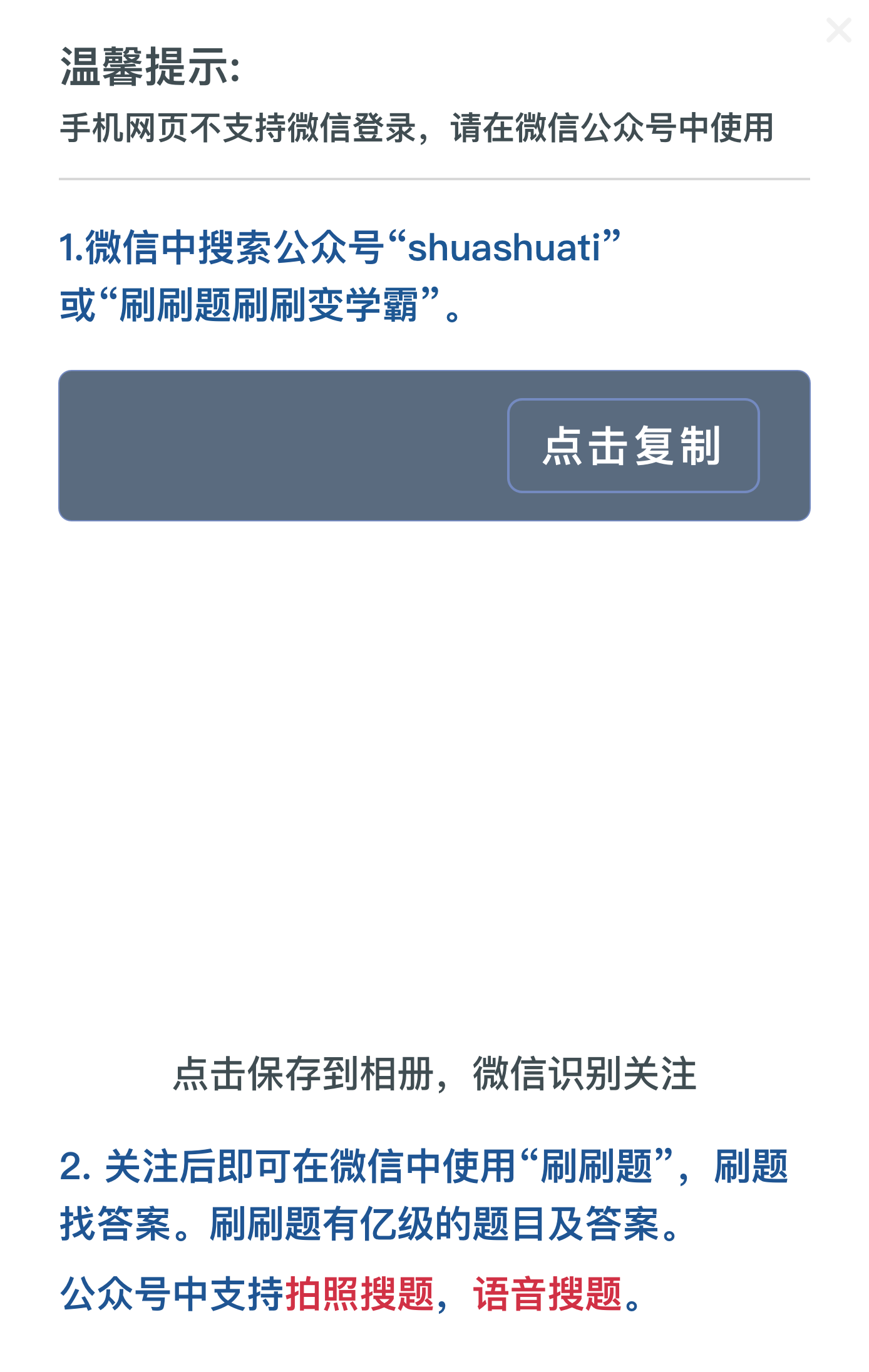

皮皮学刷刷变学霸
举一反三
【单选题】Always follow through with what you start.
A.
Interjection
B.
Conjunction
C.
Adverb
D.
Preposition
【单选题】总承包人为配合、协调建设单位进行的专业工程发包,对建设单位自行采购的材料、工程设备等进行保管以及施工现场管理、竣工资料汇总整理等服务所需的费用称为
A.
暂列金额
B.
计日工
C.
总承包服务费
D.
脚手架工程费
【单选题】Indication of Barium follow-through?
A.
Chronic constipation
B.
Altered bowel habit
C.
Megacolon
D.
Malabsorption
【单选题】现有一杂合子AaBb。如果A和B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(a和b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),且在减数分裂中始终联系在一起,并且同时传递给配子,可形成______ 种亲本型配子,比例为__________ ,这种现象称为完全连锁。
A.
四;1:1:1:1
B.
三;1:2:1
C.
二;1:1
D.
一;100%
【单选题】对发包人自行采购的材料、工程设备等进行保管以及施工现场管理、竣工资料汇总整理等服务所需的费用,总承包人应计入( )。
A.
暂列金额
B.
暂估价
C.
计日工
D.
总承包服务费
相关题目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