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皮学,免费搜题
登录
搜题
【简答题】

 我来纽约的这些年,纽约的节奏变了,性情也变了。紧张气氛加剧,更多暴戾。你可以在许多地方,从许多人脸上看到这一点。现代生活产生的挫折感,到这里就会翻番,放大—— 穿越城区的公共汽车跑上一趟,沿途的挫折和麻烦,足以让司机精神错乱:交通灯的转换总是快了半拍,乘客捶打关闭的车门,卡车挡住惟一的通路,硬币失手掉到地上,不该发问的时候偏偏有人啰嗦。气氛更紧张,速度更快。出租车跑得比十年前快了——他们十年前跑得就不慢。从前出租车司机乐呵呵的,如今他们时不时地很疯狂,像是有今天没明天。在进入城里的西区高速路,驾车人懵懵懂懂地随大流而行——那种无可逃逭的运动很是刺激,后面有人催,两侧给人夹裹,你的车像一片木屑在磨坊的水流中载浮载沉。 纽约从未像现在这样糟心、拥挤、紧张。钱多得是,纽约的反应也不慢。餐馆很难挤进去,经理们为了夫餐馆的一顿午餐,乖乖门口,如同失业者排起长龙,只为领一碗热汤。(繁荣期人们排队等一口吃的,萧条期也一样。)曼哈顿的午餐时间提前了半小时,始于十二点或十二点半,指望能先于众人抢得一席之地。人人下班时间都比以往饿了一点。公寓“恕无空房”的告示。第五大道的公共汽车上,只有站立的份儿,而从前每个买票的乘客座位。旧日的双层汽车消失了——人们搭车再不是为了兜风。某些日子的某些时刻,几乎叫不上一辆出租车,争抢得厉害。你抓住车门把手,拉开车门,发现还有一位从另一侧长驱直入。看门人靠吹哨子调度出租车发了财,一些看门人其实无门可看——不过是在大街上溜达,见机行事,给出租车乘客拉拉车门。与以往稍许悠闲的日子相比,纽约变得不舒适,也不方便了,但纽约人原本就不在意舒适和方便——果真在意,他们会搬到其他地方。 纽约最微妙的变化,人人嘴上不讲,但人人心里明白。这座城市,在它漫长的历史上,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。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,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,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,摧毁桥梁,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,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。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: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,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。 城市的所有居民面对湮灭无存这一顽固的事实,而这一事实在纽约表现得更为集中,因为纽约本身就是集中的,还因为,所有目标中,纽约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最受瞩目。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,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、不可抵挡的诱惑力。
我来纽约的这些年,纽约的节奏变了,性情也变了。紧张气氛加剧,更多暴戾。你可以在许多地方,从许多人脸上看到这一点。现代生活产生的挫折感,到这里就会翻番,放大—— 穿越城区的公共汽车跑上一趟,沿途的挫折和麻烦,足以让司机精神错乱:交通灯的转换总是快了半拍,乘客捶打关闭的车门,卡车挡住惟一的通路,硬币失手掉到地上,不该发问的时候偏偏有人啰嗦。气氛更紧张,速度更快。出租车跑得比十年前快了——他们十年前跑得就不慢。从前出租车司机乐呵呵的,如今他们时不时地很疯狂,像是有今天没明天。在进入城里的西区高速路,驾车人懵懵懂懂地随大流而行——那种无可逃逭的运动很是刺激,后面有人催,两侧给人夹裹,你的车像一片木屑在磨坊的水流中载浮载沉。 纽约从未像现在这样糟心、拥挤、紧张。钱多得是,纽约的反应也不慢。餐馆很难挤进去,经理们为了夫餐馆的一顿午餐,乖乖门口,如同失业者排起长龙,只为领一碗热汤。(繁荣期人们排队等一口吃的,萧条期也一样。)曼哈顿的午餐时间提前了半小时,始于十二点或十二点半,指望能先于众人抢得一席之地。人人下班时间都比以往饿了一点。公寓“恕无空房”的告示。第五大道的公共汽车上,只有站立的份儿,而从前每个买票的乘客座位。旧日的双层汽车消失了——人们搭车再不是为了兜风。某些日子的某些时刻,几乎叫不上一辆出租车,争抢得厉害。你抓住车门把手,拉开车门,发现还有一位从另一侧长驱直入。看门人靠吹哨子调度出租车发了财,一些看门人其实无门可看——不过是在大街上溜达,见机行事,给出租车乘客拉拉车门。与以往稍许悠闲的日子相比,纽约变得不舒适,也不方便了,但纽约人原本就不在意舒适和方便——果真在意,他们会搬到其他地方。 纽约最微妙的变化,人人嘴上不讲,但人人心里明白。这座城市,在它漫长的历史上,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。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,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,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,摧毁桥梁,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,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。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: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,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。 城市的所有居民面对湮灭无存这一顽固的事实,而这一事实在纽约表现得更为集中,因为纽约本身就是集中的,还因为,所有目标中,纽约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最受瞩目。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,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、不可抵挡的诱惑力。
拍照语音搜题,微信中搜索"皮皮学"使用
参考答案:


参考解析:


知识点: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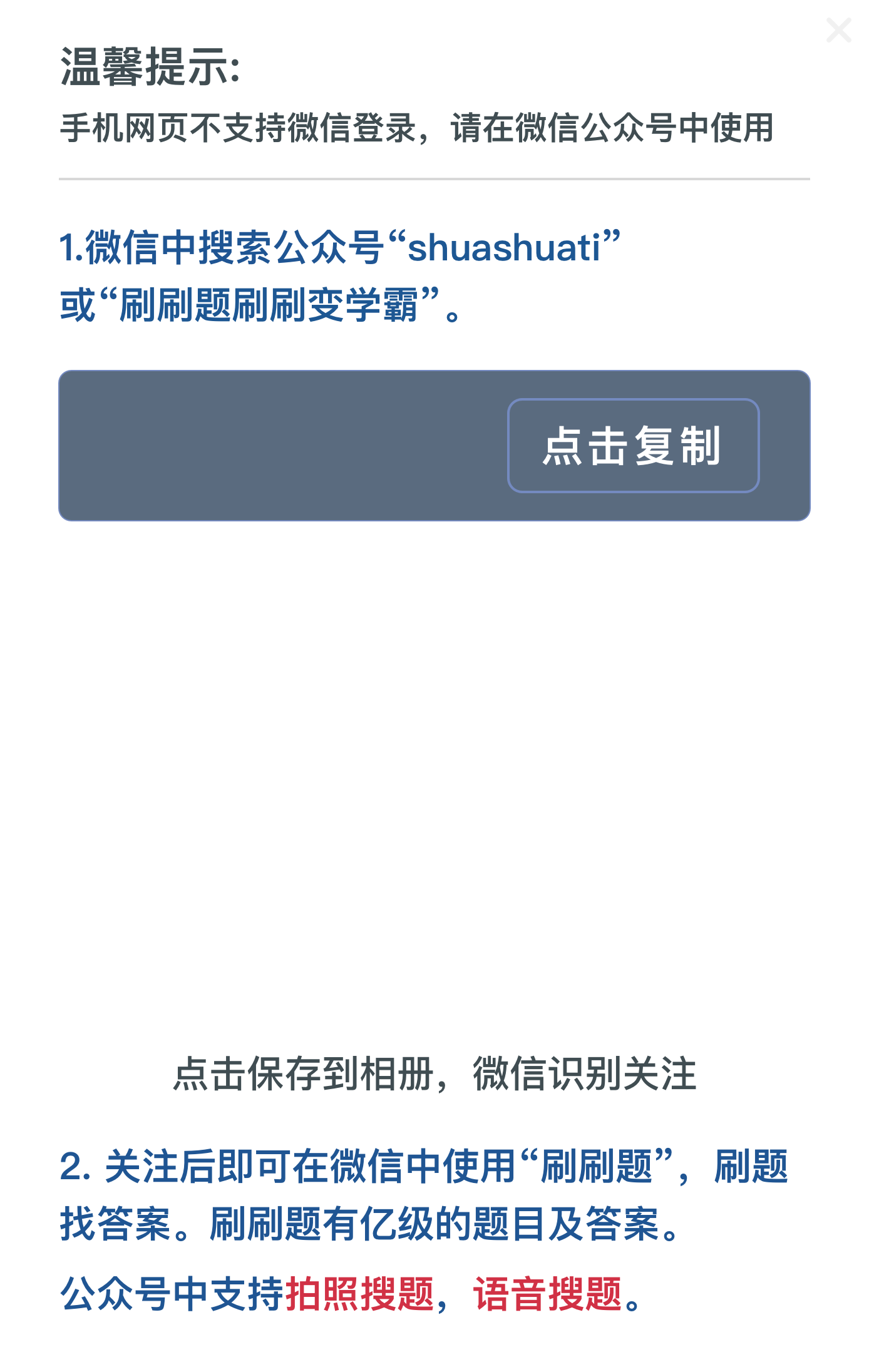

皮皮学刷刷变学霸
举一反三
【简答题】以下 () 函数不是 jQuery 内置的与 AJAX 相关的函数 @font-face { font-family: 宋体;}@font-face { font-family: 宋体;}@font-face { font-family: "@宋体";}p.MsoNormal, li.MsoNormal, div.MsoNormal { margin: 0cm 0cm 0.0001pt; t...
【简答题】用英语思考______________
【单选题】以下关于PHP的函数说法不正确的是?
A.
是对一段可以实现指定功能(运算、操作系列)的代码的封装与定义;
B.
可以使用关键词function来定义函数;
C.
函数体中必须有return语句来返回函数值给调用者;
D.
用户可以直接调用内置函数。
【简答题】分别创建4个函数:(一)2个数相加;(二)2个数相减;(三)2个数相乘;(四)2个数相除。具体要求如下: 每个函数中参与运算的2个数据,通过prompt( )函数获取。 通过prompt函数输入2个数据后,分别通过调用创建的函数,获取这两个数的和、差、积和商。 最后,将这个两个数的和、差、积和商,彼此相加之后,通过alert函数弹出。 注意函数的摆放位置 注意区分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注意是否需要使...
相关题目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