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皮学,免费搜题
登录
搜题
【简答题】

 (二) 现在,谁还能说出一棵草、一根木头的全部真实。谁会看见一场一场的风吹旧墙、刮破院门,穿过一个人慢慢松开的骨缝,把所有的风声留在他的一生中。 这一切,难道不是一场一场的梦。 如果没有那些旧房子和路,没有又落下的尘土,没有与我一同长大仍旧活在村里的人、牲畜,没有还在吹刮着的那一场一场的风,谁会证实以往的生活——即使有它们,一个人内心的生存谁又能见证。 我回到曾经是我的现在已成别人的村庄。只几十年功夫,它变成另一个样子。尽管我早知道它会变成这样--许多年前他们往这些墙上抹泥巴、刷白灰时,我便知道这些白灰和泥皮迟早会脱落得一干二净。他们打那些土墙时我便清楚这些墙最终会回到土里--他们挖墙边的土,一截一截往上打墙,还喊着打夯的号子,让远远近近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在打墙盖房子了。墙打好后每堵墙边都留下一个坑,墙打得越高坑便越大越深。他们也不填它,顶多在坑里栽几棵树,那些坑便一直在墙边等着,一年又一年,那时我就知道一个土坑漫长等待的是什么。 但我却不知道这一切面目全非、行将消失时,一只早年间日日以清脆嘹亮的鸣叫唤醒人们的大红公鸡、一条老死窝中的黑狗、每个午后都照在(已经消失的)门框上的夕阳......是否也与一粒土一样归于沉寂。还有,在它们中间悄无声息度过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光的我,他的快乐、孤独、无人感知的惊恐与激动......对于今天的生活,它们是否变得毫无意义。 当家园废失,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。 ——选自亮程《今生今世的证据》
(二) 现在,谁还能说出一棵草、一根木头的全部真实。谁会看见一场一场的风吹旧墙、刮破院门,穿过一个人慢慢松开的骨缝,把所有的风声留在他的一生中。 这一切,难道不是一场一场的梦。 如果没有那些旧房子和路,没有又落下的尘土,没有与我一同长大仍旧活在村里的人、牲畜,没有还在吹刮着的那一场一场的风,谁会证实以往的生活——即使有它们,一个人内心的生存谁又能见证。 我回到曾经是我的现在已成别人的村庄。只几十年功夫,它变成另一个样子。尽管我早知道它会变成这样--许多年前他们往这些墙上抹泥巴、刷白灰时,我便知道这些白灰和泥皮迟早会脱落得一干二净。他们打那些土墙时我便清楚这些墙最终会回到土里--他们挖墙边的土,一截一截往上打墙,还喊着打夯的号子,让远远近近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在打墙盖房子了。墙打好后每堵墙边都留下一个坑,墙打得越高坑便越大越深。他们也不填它,顶多在坑里栽几棵树,那些坑便一直在墙边等着,一年又一年,那时我就知道一个土坑漫长等待的是什么。 但我却不知道这一切面目全非、行将消失时,一只早年间日日以清脆嘹亮的鸣叫唤醒人们的大红公鸡、一条老死窝中的黑狗、每个午后都照在(已经消失的)门框上的夕阳......是否也与一粒土一样归于沉寂。还有,在它们中间悄无声息度过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光的我,他的快乐、孤独、无人感知的惊恐与激动......对于今天的生活,它们是否变得毫无意义。 当家园废失,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。 ——选自亮程《今生今世的证据》
拍照语音搜题,微信中搜索"皮皮学"使用
参考答案:


参考解析:


知识点: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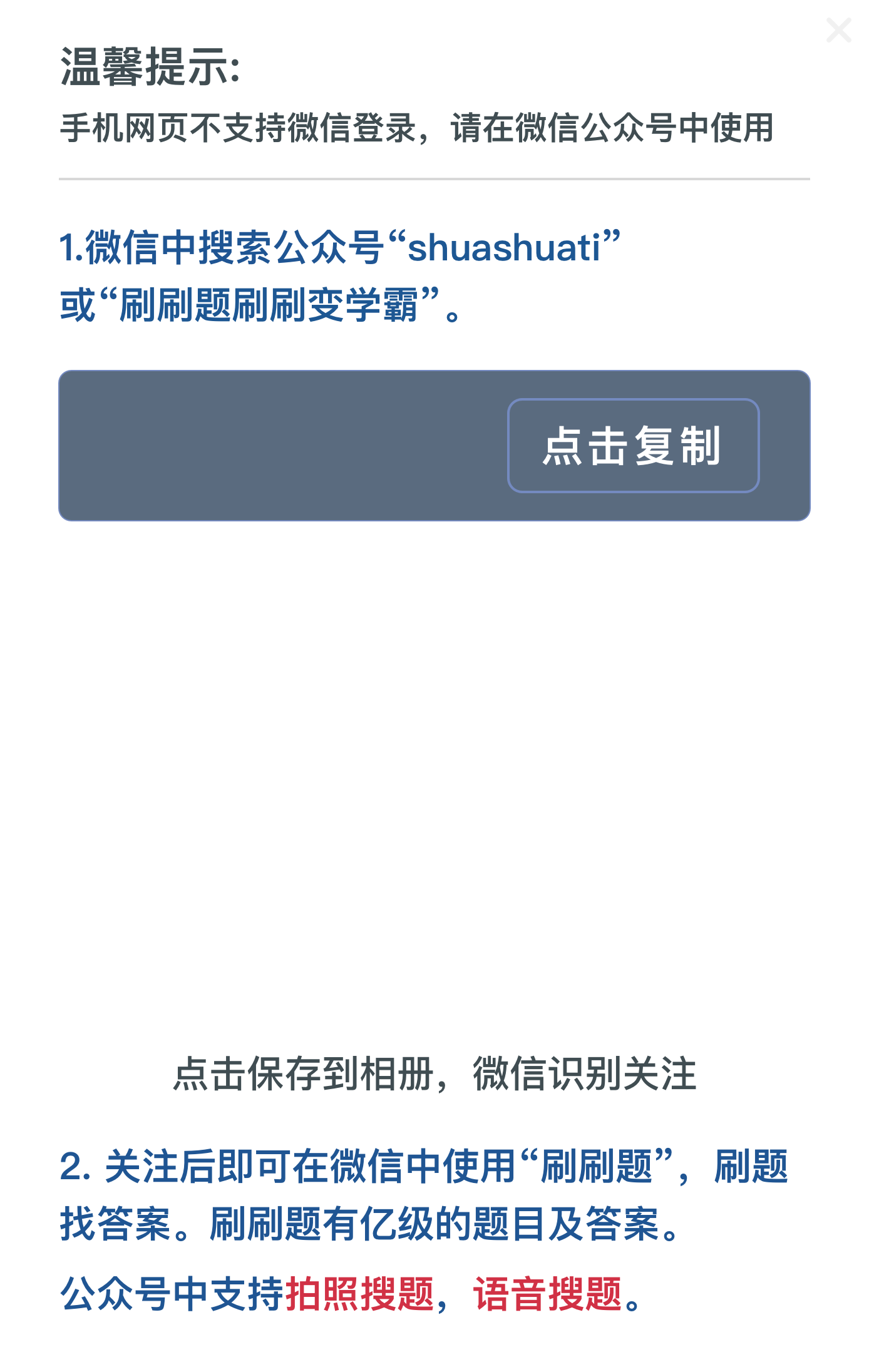

皮皮学刷刷变学霸
举一反三
【单选题】The coding sections of the gene are interrupted by
A.
intons
B.
space gene
C.
exons
D.
promoter
【简答题】• 2012 年冬 季开始,中国各地数个城市相继大雾重重,空气出现严重污染。因而被戏称为“十面霾伏”。 请以“蓝天”为主题进行演讲。
【单选题】对外开放使我国迅速实现了向国际贸易大国的转变,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( ) 1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2加快了工业化进程 3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4提升了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
A.
①③
B.
①②
C.
③④
D.
①②③④
【单选题】2019年9月23日电,中央企业优秀形象宣传片网络展播系列活动成果发布22日在京举行。活动由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指导,人民网主办,南方电网公司承办,以( )为主题,多角度、多层次、多元化地展现了中央企业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与丰硕成果。
A.
“大国新利器·阔步新时代”
B.
“大国顶梁柱·阔步新时代”
C.
“大国顶梁柱·壮丽新时代”
D.
“大国顶梁柱·阔步新征程”
相关题目:
【单选题】The coding sections of the gene are interrupted by
A.
intons
B.
space gene
C.
exons
D.
promoter